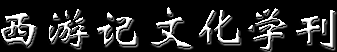 (第一辑)
(第一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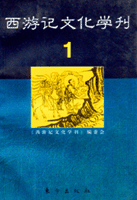
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作者,的确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要真正把握作品,就必须认识作者,所以古人讲“知人论世”。同样,《西游记》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主题和宗旨,因此,作者问题是研究《西游记》必须首先要解决的。由此可见,《西游记》的作者之争,决不仅仅是一个个别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思想的较量……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章培恒
至迟在元末明初就已存在着一种名为《西游记》的小说。国内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今天所见的百回本《西游记》就是吴承恩在这基础上写成的。但国外的研究者对于百回本《西游记》出于吴承恩之手这一点还有持慎重态度甚或加以否定的。例如,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小川环树氏在《〈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中就认为:必须确切地证明了百回本《西游记》中的方言是淮安方言,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才能获得有力的旁证。另一位对《西游记》作过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氏则干脆认为百回本《西游记》并非吴承恩所作。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海内外的学者。
一
从现有的各种《西游记》板本来看,《西游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却没有一种是署吴承恩作的。署名为吴承恩作,实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所出现的铅印本《西游记》。其所以这样署,乃是依据鲁迅先生和胡适的考证。但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的。
他们用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在那里有着如下的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需要注意的是: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国的历史上,两种著作同名并不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甚至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两种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发生过。例如,清初就曾有过两部《东江集钞》,一部的作者是沈谦,另一部的作者是唐孙华。在小说中,两书同名的事也有。在明代有过一部秽亵小说《如意君传》,在清代另有一部《如意君传》,却非秽亵小说。总之,如果没有有力的旁证来证明《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乃是百回本小说,也就无法确切地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有如下的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倘若《千顷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吴承恩的《西游记》乃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与唐、沈二人的著作属于同一性质,换言之,它确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著作。
当然,吴承恩是否有可能写一部名为《西游记》的游记?回答是:有此可能。如所周知,吴承恩曾被任命为荆府纪善,也就是荆王的属官。荆王府在蕲州,吴承恩从其故乡淮安去荆王府赴任,乃是从东往西行。假如他写一游记性的作品,记述其赴任途中之所经历,而名之为《西游记》,那是毫无不合理之处的。同时,像吴承恩那样一位“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吴承恩传》)的文人,在经过这样的长途跋涉之后,写些游记,更完全是情理中事。
第二,《千顷堂书目》的著录是否可靠?由于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如果他知道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通俗小说,绝不会把它编入地理类去。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只是依据书名,就想当然地把它编入了地理类。这牵涉到《千顷堂书目》的性质。张钧衡为《千顷堂书目》写的《跋》说:“……钱受之采明诗,从俞邰(虞稷的字。——引者)借书,得尽阅所未见,又为作《千顷斋藏书记》。是俞邰实有是书,并非悉据旧目。”这就是说,《千顷书目》所著录的,乃是黄虞稷所收藏的图书。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也持同样看法。据此,黄虞稷自应藏有吴承恩的《西游记》,从而也就不会因没有看过此书而仅据书名胡乱分类。至于他之不注明《西游记》的卷数,也可能是该书并未分卷,或黄氏所得为残本,全书卷数不明,并不能据此而断言虞稷未见该书。
但是,由于《千顷堂书目》著录的书甚多,似乎不是私人之力所能有,而且,钱谦益的《千顷斋藏书记》也只说虞稷有藏书六万卷,《千顷堂书目》的著录显然超过此数,有些研究者就认为:该书著录的并不都是虞稷的藏书;虞稷的目的是要编《明史艺文志》,因而把他所知道的明人著作的目录全都列入了,其性质类似于焦羟的《国史经籍志》。我想,这种看法未必正确。黄虞稷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期,书籍价格必然极其低廉,何况一般的明版在当时只能算普通书,因此,以私家之力而收集到这么多明人著作,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虞稷也许确有编《明史艺文志》的雄心,但这并不能证明《千顷堂书目》著录之书并非其所收藏。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说:“《明史艺文志》之撰集,凡经五变。焦宏创始于前,不分存佚,通记古今。黄虞稷搜藏于后,兼补前朝,殆尽目睹。”也就是说,虞稷虽意在编《明史艺文志》,但《千顷堂书目》著录的,乃是其藏书(所谓“搜藏于后”),殆皆黄氏所“目睹”。汪辟疆先生《目录学研究》也说:“虞稷生际明季,时值南都倾覆,天府之宝藏,故家之秘笈,尽力搜罗,典籍大备。乃就有明一代之书,详加著录。为《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至于其著录数超过《千顷斋藏书记》的记录,当是在钱谦益写作此文后,虞稷仍在不断地增加收藏。尤其重要的是:从明人所撰的书目来看,像《千顷堂书目》这样的名称,当与《宝文堂书目》、《世善堂书目》、《红雨楼书目》等属于同一类型,为私人藏书目录;倘是《国史经籍志》那样的性质,似不应以私家之堂作为书名。所以,否定《千顷堂书目》为私家藏书目录,理由似乎并不充分。退一步说,即使它确是《国史经籍志》那样的性质,但既然黄虞稷是著名的藏书家,也就不能排除虞稷确实藏有吴承恩《西游记》的可能;纵或他确未藏有此书,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之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乃是毫无根据的瞎编。
综上所述,我们若要肯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除了必须有足够的旁证来证明《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是小说外,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千顷堂书目》关于此书的分类是错误的。而鲁、胡二氏的考证皆未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二
作为鲁、胡二氏上述考证的最重要的佐证的,是清代吴玉扌晋的《山阳志遗》和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现先引《山阳志遗》的记载于下:
天启旧志列先生(指吴承恩。——引者)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由此可见,吴玉扌晋之所以断言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其依据就是天启《淮安府志》(以下简称天启《志》)中的《淮贤文目》,但他并未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乃是通俗小说。当然,他注意到了《西游记》中的方言,但即使这确能证明此书“出淮人手”,又安见其必为吴承恩(因为“淮人”很多)所写,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的。何况书中的方言也并不能证明百回本《西游记》出于淮人之手,具体说明见后。
另一方面,只要仔细地读一读上引的文字,就可发现:吴玉扌晋并不是要拿书中的方言来证明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乃是通俗小说,而是先肯定了见于天启《志》的《西游记》之为小说,然后再以小说《西游记》中的方言为依据,进而论述此书到底是吴承恩作抑丘处机作的问题。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尚有待于证明。而正因为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未作论证,他的论断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现再引阮葵生《茶余客话》的有关记载于下:
按,旧《志》(指天启《志》。——引者)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阮葵生跟吴玉扌晋一样,也是先断定天启《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为“通俗演义”(即百回本小说),然后再引书中方言作为旁证。而对于天启《志》著录的《西游记》到底是否小说的问题,他同样没有作任何论证。因此,阮葵生之说在这方面丝毫没能弥补吴玉扌晋之说的缺陷。其实,阮葵生恐怕连天启《志》都没有查,其引天启《志》乃是据吴玉扌晋之文转引的。所以,吴玉扌晋引天启《志》时,把原文“复善谐剧”误为“复善谐谑”,而阮葵生的引文同样作“复善谐谑”。
其后,丁晏的《石亭记事续编》对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也有考证。他除了据书中的明代官制进一步证明此书不可能为丘处机所作外,其余均与吴、阮如出一辙,原文避繁不引。而鲁迅先生与胡适对这问题的考证,又均不出吴、阮、丁三人的范围。总之,他们都未能排除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乃是游记性质的作品的这种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实嫌证据不足。
三
吴玉扌晋所说的“书中多吾乡方言”这一点虽未能作为天启《志》著录的《西游记》为百回本小说的确证,但这问题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吴、阮、丁三人都未说明书中的哪些词语是淮安方言,但幸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注释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手头所有的是1980年5月的北京第二版。从该本的注释来看,明确提及淮安方言的共六处,在卷首《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中提及的一处;另有若干条只注为“方言”而未明言“淮安方言”,当是未能确定其为何地方言。现将其明确提及淮安方言的七条引录于下,所注页码,皆指该本。
(一)“骨冗”本是淮安方言,形容婴儿在母腹内蠕动。现代语写作“咕容”。(见《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按,这是对五十三回“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一语的说明。)
(二)犯头,是冒犯的由头。淮安方言:无意触怒对方而引起对方的误会,就对方说,叫做“认犯”或“认此犯头”。犯亦作泛,见后文第三十一回。(见29页注一。按,这是对第三回“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一语的注释。)
(三)倒踏门——男人在女家就亲。今淮安方言叫倒站门。(96页注一)
(四)是——淮安方言,语尾词。如后文第三十一回“柳柳惊是”。(181页注三。按,这是对第十四回“倒也得些状告是”的注释。)
(五)木圈户——淮安方言,烂糊的意思。(449页注一)
(六)畜——淮安方言:熏、呛。第六十七回又写作“旭”。(577页注一)
(七)山恶人善——淮安成语,地理环境虽然险恶,居民却很善良。(609页注二)
在这七条中,前四条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一,认为“骨冗”就是现代汉语的“咕容”,是很正确的。《新华字典》即收有“咕容”,释为“象蛆那样地爬动”,并且没有把此词作为方言处理,足征“咕容”并非方言。在普通话中,“咕”“骨”同音,“骨”字的有一种读法,连声调也跟“咕”相同(皆读gū);“容”与“冗”也同音,唯声调略有区别,“容”为阳平,“冗”为上声。换言之,“骨冗”不过是“咕容”的另一种写法,从而也并非方言。把“咕容”写成“骨冗”,至多只能证明在作者的方言中,“容”、“冗”属于同一声调。但“容”、“冗”属于同一声调并非淮安方言所特有的现象,所以也就不能把“骨冗”看作仅仅是淮安方言。可能注释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正文的注释中仅仅把“骨冗”释为“方言”,而没有释为“淮安方言”,见681页注一。
第二,从关于“犯头”的注释中“犯亦作泛,见后文第三十一回”之语,可见注释者认为第三回的“认此犯头”就是第三十一回的“认了这个泛头”(见397页)。我也认为从上下文来看这两者应是同样的意思,而且在普通话中“犯”与“泛”同音、同声调,“泛头”当为“犯头”的另一种写法。但三十一回所写的情况是这样的:猪八戒和沙和尚把黄袍怪的两个儿子从云端里掼下去,并且叫道:“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老猪与沙弟拿将来也。”黄袍怪听后,心中暗想道:“猪八戒便也罢了;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他怎么得出来?我的浑家怎么肯放他?我孩儿怎么得到他手?这怕是猪八戒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故将此计来羁我。我若认了这个泛头,就与他打啊,噫,我却还害酒哩!”由此可见,猪八戒是故意去激怒他的,并非如“犯头”注所说的“无意触怒对方而引起对方的误会”。换言之,若把《西游记》中的“犯头”视为淮安方言,那么,在第三回中虽还可通,在三十一回中就通不过了。
第三,“倒踏门”的“踏”与淮安方言“倒站门”的“站”,字音、字义全都不同。“倒踏门”显然不能视为淮安方言。
第四,把“是”作为语尾词使用,并不只限于淮安方言。在长江以北其他地区的方言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南通方言中就有(此条承陆树仑同志见示,谨此志谢;他是南通人)。
由此看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明言淮安方言的七个词语中,至少有四个不是淮安方言,或不能仅仅作为淮安方言。应该承认,《西游记》的注释者在这方面是花了相当大量的劳动,而且对淮安方言是相当了解的,但从《西游记》的注释来看,作品中真正能作为淮安方言的词语,至多只有三个,即“木圈户”、“畜(旭)”和“山恶人善”。所以,作品的真正淮安方言,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而且,由于我们并未对长江以北的地区的方言作普遍调查,上述的三个词语是否为淮安方言所独有,也还是问题。总之,吴玉扌晋的所谓“书中多吾乡方言”,阮葵生的所谓“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至少是并不确切的。
当然,在百回本《西游记》中,确有相当数量的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包括上述淮安方言在内)。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吴语地区的方言。现举一些明显的例子:
一、“圆丢丢”,见43页。按,此为吴语中形容圆形物体之词。
二、“掮”,在书中多次出现,见778页、782页、835页、948页、949页等;有时也写作“搴”,见412页、413页、776页、780页、859页等(按,776页写孙悟空把芭蕉扇“搴在肩上,找旧路而回”,778页则说“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足见“搴”为“掮”的一另一种写法)。“掮”为吴语方言的常用词。
三、“拗”,见326页:“把清油拗上一锅。”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于此有一条注:“拗(yǎo)——用勺取水叫舀。拗,舀的同音字。”按,在普通话中,拗的注音为ǎo,而非yǎo。在古代字书中,拗有“於教切”、“於绞切”等读音,但作为反切上字的“於”,是读作“乌”的,所以,拗与舀并非同音。换言之,把拗的读音注作yǎo,视为舀的同音字,似乎并不确切。而在吴语地区的方言中,确有称“用勺取水(或油)”为“拗(ǎo)的。要装上一锅水(或油),在以前一般都要用勺。因此,“把清油拗上一锅”的“拗”当为吴语方言。又,若是用其他器具取水,在吴语方言中也不称为“拗”。而《西游记》339页写到用玉瓢、玉酒杯取水,就称为“舀”而不称为“拗”了。足见作者对吴语方言中的“舀”、“拗”的区别非常熟悉。
四、“替”,见1172-73页:“行者道:‘我解得(《多心经》,我解得。’……(八戒)说道:‘嘴巴!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里禅和子,听过讲经,……说甚么晓得、解得!’”又,1174-75页:“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这里的两个“替”字,都作“与”字解释。把“与”说成“替”,乃是吴语方言中的现象。
五、“该”,见216及217页:“活该三百多余岁”,“整整压该五百载。”按,在某些吴语方言中,“该”字接于动词之后,含有“在那里”之意。例如,我们听宁波人谈话,有时就会听到这样的对话:“某人还活该否?”“活该。”或者:“咸菜上的石头压该否?”“压该。”“压该多少时光了?”“压该半个月了。”《西游记》中的这两个“该”字,只有作为吴语方言,才解释得通。
六、“身单”,见493页:“只见廊庑下,横身单着一个六尺长躯。…原来是个死皇帝,……直挺挺睡在那厢。”此一“身单”字,显然为躺、睡之意。按,在一般的字书中,“身单”字皆释为“垂下貌”,也可作为“躲”字使用,无释为躺、睡者。唯在吴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用法。《海上花列传》第二回:“(王阿二)便说:‘榻床浪来身单身单哩。’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向下……”可证。
七、“跄”,见254页:“八戒调过头来,把耳朵摆了几摆,长嘴伸了一伸,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乱跄乱跌。”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于此有注说:“跄——这里是形容行路歪斜的样子。”按,“踉跄”一词有行路不稳之意,单独一个“跄”字并无“行路歪斜”的意思。吴语方言中“跄”为奔跑之意;此处“乱跄”,实为吴语。盖“那些人”被八戒惊吓以后,胆小的已吓瘫了(“东倒西歪”),胆大的则尚能奔跑,但因害怕之故,一面奔,一面跌。
八、扌冈,见724页:“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扌冈住钯齿。”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释说:“扌冈——同扛。扌冈住,顶住。”按,“扌冈”确是“扛”字的另一种写法;从上下文看,此处的“扌冈住”也确是顶住之意;但“扛”字在字书中并无“顶”的意思。唯在吴语方言中,有一与“扌冈”相近的音(其音大致相当于上海方言中的“戆大”的“戆”),其义为两物相顶。此处的“扌冈”字,当即吴语方言。因吴语方言中的这个音,无法以方块字来准确表示,故只得用音读相近的“扌冈”字。
九、“等”,见1075页:“三藏与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们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按,当时三藏、行者都已在被人抬着走,行者为什么还要说:“等他抬”呢?根据“等”字的一般意义,此句显然是不通的。但在吴语方言中,“等”有“随”、“让”的意思,“让他去”可以说成“等他去”。所以,此处的“等他抬”实为吴语方言,即随他抬、让他抬之意。
十、“安”,如594页:“将核儿安在里面。”600页:“这行者双手爬开肚腹,拿出肠脏来,一条条理够多时,依然安在里面。”984页:“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此等“安”皆“放置”之义。称“放置”为“安”,也是吴语方言。
以上十例,仅是百回本《西游记》中所用吴语方言的一部分。我请教了好几位苏北地区的同志,包括三位六十岁左右的淮安同志,得知在淮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方言中,都不这样使用。当然,由于我没有对苏北地区的方言作过广泛调查,上举的十例中,可能有少数也见于苏北乃至淮安地区的方言,只不过我所请教的这几位同志不知道罢了。但可以相信,它们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淮安方言;或者说,大多数都不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
由此可见,百回本《西游记》中,实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
四
因为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前,至少已出现过一种题为《西游记》的比较简单的本子,百回本《西游记》即以此类本子为基础,加工而成,所以,造成百回本《西游记》中两种方言并存的现象的,实有三种可能性:一、百回本所据以加工的底本中,原有这两种方言;二、底本中原有一种方言,百回本的作者在加工时又增添了另一种方言;三、百回本的作者精通两种方言,它们全都出于他的手笔。
吴承恩是淮安人,又当过长兴县丞,自有精通这两种方言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先肯定了百回本《西游记》出于吴承恩之手,然后才能以他精通两种方言为理由来肯定上述的第三种可能性。而如上所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出于吴承恩尚是一个有待证明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所以,为了判断这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足以成立,我们必须将百回本跟它以前的本子加以对照。鲁迅先生曾把朱鼎臣本作为早于百回本的本子。这一说法被郑振铎先生否定后,鲁迅先生也接受了郑振铎先生的观点。但后来澳大利亚籍的柳存仁教授又为鲁迅先生早先的观点辩护,并且也有相当的理由;看来这仍是一个尚未最后解决的问题,不过,既然对于朱鼎臣本的时代问题尚无一致的结论,我们也就不能拿它来跟百回本相对照,而只能把《永乐大典》所收的那一段《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作为对照的依据。现将原文引录于后:
长安城西南上,有一条河,唤作泾河。贞观十三年,河边有两个渔翁,一个唤张梢,一个唤李定。……(以下略,编者按)
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把这一千二百字左右的原文全部引录,是希望读者跟我一起从头到尾地检查一下,看其中可有任何吴语方言的痕迹。应该说,在这一长段文字中并未夹杂吴语方言。但是,使用了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这一点却是明显的。“吊下一只龙头”的“吊下”无疑是“落下”之意。它是北方话,而非吴语方言。不过,在当时已有“官话”,而“官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因此,这段文字中的“吊下”一词,也可解释为南方的作者在使用“官话”。比较起来,“把五十两银来”一句中的“把”字更值得注意。由于这句中除“把”以外别无动词,它显然不是所谓“把字句”。在苏北方言中,“把”字可以作“给”解释;此句中的“把”,也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至于“来”字,显为句末语气词。把“来”字作句末的语气词用,在运用北方话的元杂剧中也常见,如《陈州粜米》的“这金锤是谁与你来”。《窦娥冤》的“都是为你孩儿来”,皆是其例。
现在再看百回本与此段文字相应的部分(见于第九回及第十回)。由于百回本中的这部分已经发展为好几千字,无法再全部引录原文;但在这几千字中,绝无任何长江北部地区方言的痕迹,读者可以覆按(其中曾出现过一个“俺”字,但此字早就成为书面语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典》本中的北方话的痕迹也被删除了。“把五十两银来”一句的删去,乃是由于情节的变动,可不置论。“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来”被改成了“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第十回),却特别值得深思。前八个字完全是照抄的,“一只”改成“这颗”是情节改动的需要(在百回本的这段文字中,唐太宗先看到龙头,然后再由其臣下向他报告“千步廊南”云云,故改“一只”为“这颗”,以与上文呼应),加一“里”字是为了使语气更顺,但为什么要把“吊下”改成“落下”呢?这两者不完全是同样的意思吗?再说,在百回本中,比“吊下”生僻得多的方言(例如上文举出过的木圈有的是,为什么它们都保留着,却非把“吊下”改掉不可?看来,百回本作者之改“吊下”为“落下”,并非出于故意。另一方面,由于“千步廊南”等八字是完全照抄的,“云端”句的因袭之迹也很明显,可以认为,百回本的作者在写这几句时,手边一定放着其所据以加工的底本,一边看,一边写。那么,底本既作“吊下”,,为什么会被他不经意地写成了“落下”呢?唯一可能是:他对于使用“落下”一词比用“吊下”更为习惯。从这点来看,百回本作者为吴语方言区的人的可能性实较其为淮安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吴语是用“落下”而不用“吊下”的,淮安方言则多用“吊下”。
百回本这一部分中由作者所增添、改写的文字不但毫无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而且还有一处使用了吴语方言,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此处见于第九回:
……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117页)
从上下文义看,“看虎”之“看”绝不能释为“观看”、“看待”或“看管”、“看守”,而当是提防之意。据《现代汉语词典》,“看”字在作为提防之意来使用时,乃是“用在动作或变化的词或词组前面,提醒对方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好的事情或情况”;也就是说,其后面不会只接一个名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这种解释,不但符合普通话中使用“看”字的习惯,也符合古代一般口语的情况。例如《红楼梦》二十八回:“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其使用“看”字,就是如此,但在吴语方言中,“看”字在作为提防、当心之意使用时,其下也可单接名词。我幼年住在家乡绍兴,当我玩弄小刀之类的物件时,长辈就会说:“要勿弄,看手(或“看手里”)!”在夏天要经过杂草丛生之处时,有时也会听到“小心,看蛇!”一类的叮嘱。此类“看”字,皆为提防、当心这意,但其下皆仅接名词。所以,百回本的“看虎”,显然属于吴语方言(此句似宜标点作:“上山仔细,看虎!”)有人也许会说:吴承恩既在长兴做过几年官,在其作品中使用句把吴语方言,也属情理之常。但是,作为淮安人的吴承恩,仅仅于中年时期到长兴去生活过几年,即使由此学会了吴语方言,而对他来说的,淮安方言一定更为习惯。若百回本确系他的手笔,在由他所增添的这好几千字的长文中,竟然只有吴语方言而没有一处淮安方言,并且还把淮安方言习用的“吊下”改为吴语方言习用的“落下”,这却很难说是情理之常。
综上所述,我们若把《永乐大典》中的这一段《西游记》与百回本中的相应部分相比较,就可得出以下的结论:在百回本以前的《西游记》中,本存在着苏北地区的方言,却无吴语方言;经百回本中两种方言并存的原因所提出的三种假设,其第二种(两种方言分别出于两种本子)得到了证实,其他两种则无法证实。自然,由于保存下来的足资比较的资料太少,用以证实第二种假设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从现有的资料中,只能找到证实第二种假设的证据,而没有足以证实其他两种假设或否定第二种假设的证据。
换言之,《西游记》中的方言并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为淮安人,倒是提供了若干相反的证据。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百回本小说?凭什么来否定《千顷堂书目》关于此书的分类?
五
为了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有的研究者还举出了另外几条旁证。这些旁证虽无多大说服力,但在这里也一并考察一下。
先看第一条旁证。
吴承恩著有《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见他熟悉并喜爱二郎搜山的传说,而百回本《西游记》也写到二郎搜山。有人就把这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一条旁证。
现先录《二郎搜山图歌》原文于下:
李在惟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众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名鹰攫拿大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禽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骤!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空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家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无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
据此,《二郎搜山图》为李在所绘。李在为明代宣德时的画家。他在当时将这故事绘为画卷,足见此一传说在明代前期就颇流行。换言之,在明代熟悉、喜爱此一传说的人当不在少数,绝不会只是吴承恩一位。既然如此,怎能把百回本《西游记》中写到二郎搜山这一点作为此书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此其一。其二,《二郎搜山图歌》称二郎神为“清源公”,可见在二郎神的几个称号中,吴承恩最喜欢或最习惯于使用的,就是这一个。而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却称之为“显圣二郎真君”(68页)、“显圣真君”(69页)、“昭惠英灵圣”(70页)、“昭惠二郎神”(71页)等等,从未称为“清源公”,这又可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不喜欢或不惯于使用(甚或根本不知道)“清源公”这一称号的,因此,很难说他跟吴承恩是一个人。第三,百回本《西游记》虽写了二郎神与孙悟空的战斗,但真正提及“搜山”二字,却是在第六回之末,二郎神捉住孙悟空之后。“真君道:‘贤弟……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待我请了赏,讨了功,回来同乐。’四太尉、二将军依言领诺。”(76页)至于搜山的具体过程,并无一字交代。直到第二十八回,才对此一“搜山”的后果略加补叙:“那(花果)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353页)而据《二郎搜山图歌》,《二郎搜山图》所绘的正是二郎率众搜山的具体经过;从该诗来看,吴承恩对图卷所绘的这一具体经过已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颇为赞赏。若百回本《西游记》确为他所作,揆以常情,他在写到二郎搜山时,对于印象很深刻的搜山过程不当一无描述,反而避开。而且,从“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之语,可见他于“搜山”之举所强调的是“放火烧坏”,而这恰恰是《二郎搜山图歌》所根本未涉及的。因此,很难说《二郎搜山图歌》与百回本《西游记》出于同一人的手笔。换言之,我们即使不把《二郎搜山图歌》作为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但至少不能把它作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
再看第二条旁证。
吴承恩的文集中有《〈禹鼎志〉序》,说明他从小喜爱野言稗史、唐人传奇,并作有志怪小说《禹鼎志》。有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他的这种情况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身份是很相应的。
按,这种情况虽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身份相应,但在明代,由于戏曲、小说的繁荣及其在文学上地位的提高,喜爱小说、作有志怪小说甚或通俗小说的人并不太少,也就是说,在这方面能够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身分相应的人并不只是很少的几个。因此,以此作为吴承恩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旁证,并不有力。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禹鼎志〉序》中的这一段话: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
据此,《禹鼎志》所写仅“十数事”,其篇幅必然不大。像这样一部篇幅较小的小说,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的结果,可见其疏懒的一斑,又怎会耗费无数的精力与时间去写百回本《西游记》这样的一部大书?此矛盾者一。其次,据其自述,在写《禹鼎志》时已只记得“十数”条奇闻,其他都忘记了。然则其写百回本《西游记》是在写《禹鼎志》之前还是之后?若在其前,那么,在写《禹鼎志》时难道连自己写过的百回本《西游记》中的许多神奇故事都已忘光?否则,为什么说自己在当时已只记得用于写《禹鼎志》的“十数事”?若在其后,那么,在写《禹鼎志》时已把原来“贮满胸中”的神怪故事忘得只剩了“十数事”,并把这“十数事”写入了《禹鼎志》中,又哪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第三,《〈禹鼎志〉序》收入吴承恩文集。天启《淮安府志》十九《艺文》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可见天启《志》的编者是看到过吴承恩文集的(否则,怎能清楚地知道这一集子的册数,而且知道它没有明确的分卷),因此,他不当不知道吴承恩尚有《禹鼎志》之作。那么,天启《志》为什么不同时著录此书?又,天启《志》还著录了吴承恩的《春秋列传序》。考《千顷堂书目》有“刘节《春秋列传》五卷”,并无吴承恩的《春秋列传序》。吴作当系为刘书所写的《序》,并非专著,故《千顷堂书目》不收。天启《志》既连《春秋列传序》这样的单篇文章都著录,为什么对单行的著作《禹鼎志》却不加著录?由此看来,天启《志》的编者当还在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故对《禹鼎志》不屑著录。但根据传统观念,通俗小说的地位较《禹鼎志》一类的志怪小说还低。倘吴承恩《西游记》是通俗小说,天启《志》的编者又怎肯加以著录?也正因此,吴承恩作有《禹鼎志》一事及其所留下的《〈禹鼎志〉序》一文,不但不能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反倒提供了若干与此相反的证据。
现在看第三个旁证。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府有云台山,山上有水帘洞,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正居住在水帘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游记》的作者把其家乡的这个洞名用到小说中去了;于是,这也被当作了百回本《西游记》系淮安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
按,《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西游记》,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但其中已把孙悟空所住之洞名为水帘洞。所以,假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之命名确是受了云台山水帘洞的影响,那也只能用来证明元末明初的《西游记》的作者为那一带人,而不能用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为淮安人。又,日本的青年学者矶部彰氏早已指出:明代何乔远编的《闽书》中,有许多地名可以使人想起《西游记》,例如:卷十五有水帘洞、铁板嶂(《西游记》的水帘洞有铁板桥),卷二十有莲花洞,卷四及卷十五皆有玉华洞(《西游记》中有玉华县),卷二十一有八角井(《西游记》中乌鸡国王被推入“八角流璃井”)等等。假如说《西游记》中的地名曾受到某些实有地名的影响,那么,与其说是受淮安的水帘洞的影响,实不如说其受福建的这一系列地名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这三条旁证也都难以成立。
现把我的看法概括如下: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明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用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论述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吴语方言时,曾引用了宁波方言和绍兴方言,但我绝不是要说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系浙江人。我认为:见于《永乐大典》的《西游记》的作者当为江苏北部人;百回本作者若是吴语方言区的人,也不无苏南人的可能。
还有一点: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的附记中,有“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之语。过去因肯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对这一记载都不加以重视。但这一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也值得研究。此“许白云”当非元代许谦,因其身分与《西游记》作者相违戾。